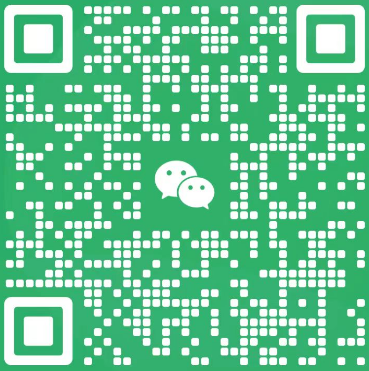当植物处于逆境胁迫下时,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氧(ROS),包括超氧阴离子、羟基自由基、单线态氧和过氧化氢(H2O2)等[1](图1)。其中,H2O2相对稳定,而且能通过水通道蛋白在不同细胞器之间运输,被认为是重要的信号分子,在植物响应逆境胁迫和生长发育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是植物细胞中抗坏血酸(ASC)-谷胱甘肽(GSH)循环中的重要酶类组分,对细胞中H2O2的清除水平起着重要作用。
APX是植物细胞中ASC-GSH循环中的重要酶类组分,以ASC为电子供体将H2O2转换为H2O,同时ASC氧化后又可通过循环还原再生(图1)。APX有多种同工酶定位在不同的细胞器中。拟南芥中曾报道有8个APXs,包括3细胞质APXs(AtAPX1、2和6);2个叶绿体APXs(基质型AtsAPX和类囊体型AttAPX)和3个过氧化物酶体APXs(AtAPX3、4和5)。但AtAPX4和AtAPX6并不编码经典的APX。AtAPX4因缺少关键的催化残基以及ASC和亚铁血红色结合位点而被重命名为APX-like(APX-L)蛋白[1]。虽然AtAPX6是一个亚铁血红素过氧化物酶,但它不需要ASC来催化H2O2,因而被认为应该归属于APX-related(APX-R)家族[2]。
作为H2O2的主要代谢酶,APX在植物生长发育和响应逆境胁迫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之前已有很多关于APX在这些方面的综述,作者在本文中也没有赘述。除了ASC,APX还能催化其他底物,如GSH、香豆酸和芥子醇等,而且还能扮演分子伴侣的角色。这也是该文重点论述的部分。
细胞质APX的活性受到多种氧化翻译后修饰(OxiPTM)调控,包括丝氨酸残基的次磺酸化修饰(-SOH)、硝基化修饰(-SNO)、硫巯基化修饰(-SSH)、谷胱甘肽化修饰(-SSG)、氰基化修饰(-SCN)、和酯酰化修饰(-SFA);甲硫氨酸残基的硫氧化作用以及酪氨酸的硝化等。
木质素合成过程中,从香豆酸到咖啡酸通常是由两个膜定位的细胞色素P450酶催化完成的。最近研究发现,二穗短柄草和拟南芥的APX具有同时氧化ASC和香豆酸的双功能活性[3](图3)。但这种双功能活性的APX在植物中的保守程度还有待研究。另外,中国白杨的线粒体APX被证明具有催化木质素单体聚合的功能[4](图3)。
ASC-GSH循环中,GSH可以自发地或在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DHAR)的催化作用下将脱氢抗坏血酸(DHA)还原成ASC(图1)。然而,兰花的APX不仅能以ASC为底物,还能将GSH氧化生成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并认为这种活性归属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活性[5]。但大部分植物的GPXs更倾向于利用硫氧还蛋白(TRX)作为底物而非GSH[6]。另外,植物中的DHAR,一些谷胱甘肽巯基还原酶(GST)和过氧化物酶(PRX)都有氧化GSH的功能。因此,兰花GPXs的底物需要进一步明确,其APX的GPX活性也需要重新定义。
除了基本的抗氧化特性,AtAPX1和水稻APX2(OsAPX2)还具有分子伴侣的功能。AtAPX1和OsAPX2的低分子量(LMW)结构主要呈现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而高分子量(LMW)的形态具有分子伴侣功能。与APX类似,植物中还存在其他几种氧化还原相关蛋白(如NTRC、GRXS17、TDX和TRX-h3),也会在HMW构象时表现出分子伴侣功能,但APX如何协同这几种氧化还原相关蛋白来响应氧化胁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植物APX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APX能代谢H2O2,但APX参与代谢了多少H2O2,不同定位的APX的贡献又如何,都待进一步阐明。这样的话,精确测量细胞中的H2O2含量就非常重要。除了OxiPTM,APX的活性也会收到非氧化的PTM调控,而且这些修饰都很短暂,这就使得APX的研究就更加困难。不难预见,除了本文介绍的新底物,APX可能还会有更多其他的底物会在将来被鉴定出来。我们对APX这个“多面手”的研究,才刚刚开始。